| 当前位置:首页>>文化长廊 |
| 那年 那月 那场雪 |
| 时间:2013-09-22 作者:郝华峰 新闻来源: 【字号:大 | 中 | 小】 |
下雪了,好冷啊!早晨一开门,院子内外白茫茫一片。天依然灰灰的,飘洒着星星点点细小的雪花。隔壁王叔起的早,戴半拉牛毡帽已经清扫完大半个院子。 娘说:“天寒地冻不能再拖了!得想办法去买些煤,要不然娃们脱活不过这个冬天。”父亲推门出去看了看雪,回来蹲在灶火旮旯叹气:“又要去借钱,而且下雪后煤更紧了,有了钱也不一定能买得上!” 娘说:“钱我想办法。大不了再求四大娘帮咱一回。到手了,明天一早你就去城里买煤。都三九天了,眼看秸秆也烧完了,如今又下场雪,难道合家人不吃饭了?”。 父亲没有做声,拖个扫帚出门扫雪去了。娘找出了一件她穿过的旧毛衣,补了颗扣子,让我吃过早饭后穿上去上学。毕竟寒风凛冽,天实在是太冷了! 这是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事。那是个极为特殊的时期。全县当时仅有一座国营小矿生产百姓用煤。县城离矿百十里远,为方便群众买煤,县里在城南设了一个煤站。夏天用煤量少、煤还容易买到,一到冬天加上取暖,煤便是十分的紧缺。一些城镇市民往往未雨绸缪夏储冬用。而我们这些家境贫苦的农民大半都靠烧秸秆干蒿度日。直到这场大雪后逼紧了父母才想办法去买煤。 娘自告奋勇和四大娘求助不是没有考虑。四大娘老伴走的早,没有儿子。两个女儿虽光景不错但远嫁外地,逢年过节来瞧瞧也就是放点零花钱。平日里四大娘跟前缺少人手照顾。有个头痛脑热,洗洗刷刷的差事娘是省不了要去帮忙的。所以在危急之时娘想起四大娘也是盲人吃饺子心里有数。 果然如娘所料全家人的希望没有落空。四大娘二话不说,从箱底层层叠叠的布包里拿出了10元钱给了我娘。晚上我看见父母都十分高兴。四大娘的慷慨资助是真正的雪中送炭。娘和父亲说:“今晚早睡,明天早点起身,一定要把煤挑回来”。 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收拾箩筐扁担出了门。娘送父亲出门后抱堆柴禾回来灶间生火,但天阴雪厚柴禾湿潮,老半天点不着,倒是流了满满一屋子烟。 早饭前后,娘进进出出了好几回,但始终不见父亲挑煤回来。中午放学后回家仍不见父亲。我问娘,娘说:“你爹今天没排上,排的人多、扑空了。娃下午跟齐老师请个假,明天和你爹一起去煤站”。 听了娘的话,我有些风帆满满的感觉。我都12岁了,还从来没为家里做点什么。现在娘看得起我,让我出动帮家里做事,说明自己已经长大了。这天晚上,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娘说:“别胡思乱想了,娃快踏踏实实睡吧,明早娘会叫你”。我才又蒙头睡去。刚合眼,似乎觉得天亮了,可睁眼看还早。如此反复数次,总算进入了梦境。迷迷糊糊间,隔壁鸡叫了。听见了娘在穿衣服下地。我醒了。 娘轻轻点着了煤油灯。费了好大劲点柴禾烧开水,并给我和父亲每人煮了两个玉米窝头,我们趁热吃完后挑着箩筐出发了。 数九寒冬、雪地冰天。夜幕中我们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向县城走。从上游百十里湫川刮来的风呼呼吹着。穿在身上的衣服薄的象一张纸,使人不由得连打冷颤。挑在肩上的箩筐随风飘悠有点把持不定。父亲挡在了我的上面拉紧了我,边走边说:“真不该让娃也来受罪”。 好在路不太长。我们离县城满打满算五里地。也就是步行二十分钟时间。不大会功夫,我们便远远看见煤站大门那昏黄的灯光。听见了等候在外噪杂的人声。 走近后才得知,尽管我们起了个大早,但还是来晚了!煤少人多、半夜来排队的人多的是。煤站发号的小窗口已经黑压压的一字长蛇阵排了老远老远。 父亲说:“箩筐先放一旁,我们要千方百计先领号。娃紧跟着我,别乱跑让人踩了”! 排队的人们在刺骨的寒风中伫立多时,一个个都冻的鼻青脸肿、搓拳跺脚。 按照煤站的规矩:买煤的人每天早上须先在大门口排队领号,然后凭号的顺序进站交费取煤。每个号可以买煤200斤。 煤站备有两辆卡车从煤矿往煤站运煤,每车每天各跑两趟,加起来也只不过20吨左右。也就是说每天仅能勉强供200人。 在寒风和焦急的等待中时间在慢悠悠地流淌。当东方渐渐有了一丝亮光之后。发号的小窗口终于打开了。 看见发号即将开始,队伍开始躁动起来。先是一些年轻人的推搡拥挤。把原有的次序挤乱了。接着人们蜂拥而上拥向小窗口。小窗口前层层叠叠伸上来无数只手,摇晃着,叫喊着。久久排队等候的人们谁也不想扑空,都想最先抢到号。煤站大门口霎时乱成一锅粥。 我和父亲也被迅猛而来的人流截断了。我象洪峰中漂浮的一颗小草一下子被拥到最前面,距离最近时几乎可以伸手触摸到那个小窗口的铁栅栏了。但顷刻间人流又后移了。我跌进了人丛的漩涡里!眼前一黑,我意识到自己被踩倒了。我挣扎,我呼喊,我拼尽全力想爬出来,但都无济于事,我的力量太微弱了。 只是瞬间的意识清醒,我已被结结实实压在五行山下,胸部似千斤重负挤压的透不出气来,片刻间便懵过去了。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,我已伏在父亲怀里。 父亲说:“娃过来了,老天保佑,娃醒了!”是煤站的巡场员吴坨子救了我。 在秩序大乱人潮蜂涌向前时,吴坨子最先发现了被推来拥去不能自主的我。估计会出事。吴坨子本想喝开众人,救我出局。但细看境势,根本无济于事。万分危急之下,吴坨子急中生智、双眉倒竖、大喊一声:妈拉个巴子!“嘶啦啦”从腰间扯出三寸宽的老牛皮皮带在人群的激流中心“噼里啪啦”一阵猛抽。打到处如刀割火灼,挨着的是道道血印。人流四散奔逃,即使年轻力壮的也都恨爹妈少生了两只脚。这才从人堆底下拉出了已经晕了的我。 片刻之后,我苏醒了。听见吴坨子还在大骂:“狗日的,有本事给老子解放台湾去!妈拉个巴子,老子绥远打过,卓资山打过,冼恒汉见过,贺老总见过,没见过你们这几个鬼毛蹬——” “今天抢到号的别打算挑走一点煤,老子在这里巡着,让狗日的再抢!” 吴坨子何以有如此神力?可挺身而出、乱中锁定?后来我才得知:吴坨子是老兵油子。1937年8月,16岁的吴坨子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120师教导团。后来在独一旅又随贺龙、冼恒汉打榆林、打绥远、打卓资山战役。身经百战、多处负伤。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打卓资山时,吴坨子为掩护首长,被敌人的炮弹皮击中头部,虽没光荣了,却在阎王哪儿转了一圈。解放后,吴坨子被安排在陕西吴堡县公安局当领导,因没有文化,吴坨子再三向组织申请回老家安身。吴坨子为人耿直豪爽,工资又高。回来后县里也颇为作难。征求意见后给他挂了个煤站党支部书记的名分,也就是个股级干部。实际上是让革命功臣坐享清闲。但吴坨子闲不住,自告奋勇干起了煤站巡场的活。 那天在吴坨子的主持下,我们父子第一个买到了400斤煤。那时每公斤煤5分钱。我在一边照看,父亲一口气往家里挑了三回。在院子里摞起高高一堆。 晚上,娘为我们生了火炉,家里热气腾腾,充满了空前的温暖和欢乐。 2012年冬至的那天,也是天空飘着雪花。按照乡俗,是上坟祭祖的日子。我来到了核桃峁上,父母坟前,想起那个难忘的冬天,那些难忘的往事,我不禁感慨万端、潸然泪出。 而今改革开放,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同样是冬天,党和政府把每户一吨优质煤无偿送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。实现伟大的中国梦,民生问题已成为当前执政的重大主题。 吴坨子2002年夏80岁时无疾而终。如今长眠在故乡苍松翠柏环绕的革命公墓里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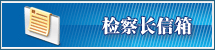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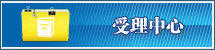  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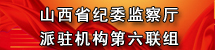
|
|
   
|